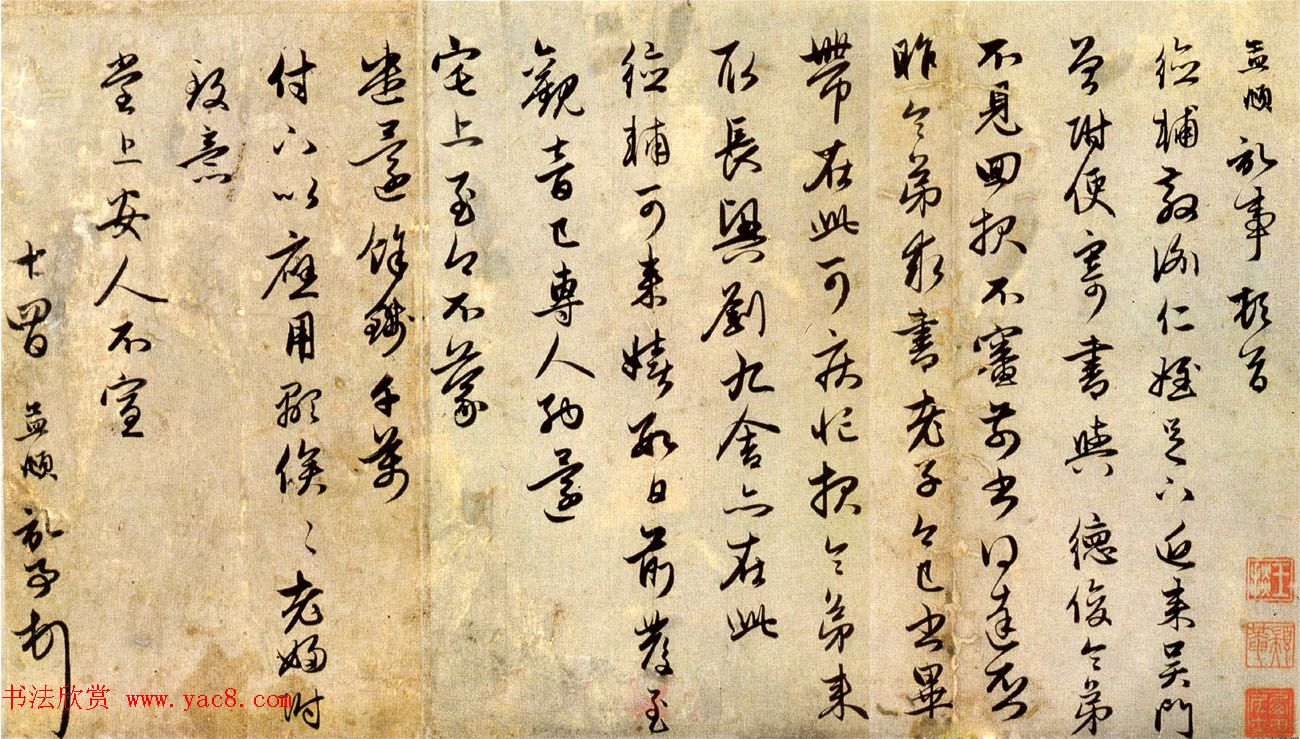《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与文化建构学术研讨会论文》
中国美术馆在2011年11月举办“首届当代名家书法提名展”,并召开“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与文化建构学术研讨会”,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说明作为中国美术界的最高展事殿堂、美术界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之一,中国美术馆对书法艺术的重视已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另一个意义去解读,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判定,即中国书法的学术地位,在我国的大美术圈中进一步得到肯定和认同。这是十分可喜可贺的。衷心祝愿提名展和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也衷心希望中国美术馆对书法学术的介入,能引入美术学科多年的经验,进一步提升书法学术活动的学术品格,引导和推动中国书法的学术活动,向更高、更科学、更深入的境界发展。
“首届当代名家书法提名展”和“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与文化建构学术研讨会”都是规格很高的学术活动,高手荟萃,名家如云。这是我讨教学习的好机会。近年来,因为从事书法教学工作,也经常有一些思考。有一些问题,深觉非一人之力可以深究,故此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今天想谈的问题是书法的边界和标准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书法的边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书法艺术事业可以说发展喜人。各种大展大赛连续不断,书法出版物充斥书店,学术研讨也很活跃,刊物、报纸、网络,宣传的力度也很大。一个新兴的文化行业,正在形成规模。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有可忧的方面,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单一纯粹的中国原生艺术体系遭遇挑战。书法行业也是观念众多,取向不一。艺术审美的多元化,为大众提供更多的审美选择,本来应该是好事。但是不同的艺术家、艺术“主义”,不免有时持论失中,张冠李戴,甚至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已在社会中造成一些观念混乱,导致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误解。因此我想,书法的边界问题,尽管是很基础的问题,还是有必要提出一辩。
书法的边界应该划在哪儿呢?
如果我们经常关注媒体,特别是一些文化先锋媒体,我们会感叹:现在的书法界可以说确实是百花齐放、流派纷呈。除了我们大家都认同坚守的、现在在我们书法界仍占绝对优势的被称为是“正统派”的书法,当代“书法”正以其五彩斑斓的颜色,装点我们的书法围墙.——“书法主义”、“学院派书法”,还有诸多贴着书法标签的“非纸上书法”,如所谓的“书法”装置艺术、“书法”行为艺术等等,也相当活跃。这些,界外人从广义的文化的视角看,都可以说是构成我们“当代书法”的文化边界。最惊世骇俗的“书法”——“人体书写秀”,不管社会舆论是视之为闹剧、还是艺术创新,人们总是认为:这是从你们书法那儿来的。因此我们在当前,还是很有必要强调:书法有书法的“边界”。
我认为:中国书法是一种以汉字为载体、通过具有特殊笔墨韵味的汉字形象的创造,表现艺术家情感的艺术。中国书法最核心本质的特征,是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汉字顺序书写。随着汉字有语义的顺序书写,形成特定的书法审美形式之链;书法线条的力量美、点画形式的外形美、点线面组合的造型姿态美、由汉字形象连结而形成的整体布局空间美,等等。这些,都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汉字顺序书写”中实现的。这是中国书法历千代而不变的模式,亘古常新。它的基础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生活原型——汉字书写行为的实用功能的实现。因为中国书法艺术是两栖的,它既是一种纯艺术,又是一种实用艺术;纯艺术的身份,正如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所说:“文字者……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1]是后起的。在历史上,汉字书写——书法——的生活功能的实现是第一义的;“翰墨之道”——书法——将汉字书写“加之以玄妙”而形成的艺术,是第二义的。因此书法脱胎于于、依托于实用汉字书写这一历史事实,就决定了书法艺术的天然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汉字顺序书写”。
如果大家认为这样一种历史引证是合乎逻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此为准的,来衡量当前形形色色的“书法”,看看哪些东西是什么,哪些是地道的书法,也许就应不当为难事了。
二、 “当代书法”审视
我认为,当代中国书法的现状是“主流突出,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民族,在历经百年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特别是经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必然的结果。多元的书法,按照其艺术理念和特征,大体可分为:
1、“正统派“:是中国当代书法的主流。他们根植经典(从先秦铭刻文字到汉碑、二王、颜柳、苏米等,延续碑、帖体系),忠诚于中国书法传统经典话语体系,从取法对象到艺术形式、创作方法、审美理想、评判标准,都延续、承袭了中国传统书法中的正统。艺术发展的思路是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先临摹经典,继融裁百家,变化出新,而自立门户。当代书坛的大家——不久前去世的启功先生、刘炳森先生,和在世的当代诸多名家,都是承继正统的代表。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的精英,是长期甘于寂寞、坚守历史正统的成果;他们使中国书法的发展在经历二十世纪“文化浩劫”的中断后,又爝火相传。
2、“流行书风”:“流行书风”涵盖面很广,前后也在变化中,有往左靠近明清诸贤,就接近了正统派,有往右靠近“少字数”,就接近了“现代派”,似乎没有明确的边界。以个人浅见,“流行书风”可称“民间俗书派”可能更准确。这里的“俗”不是低俗,而是“质朴”、“粗朴”,与正统的“雅”相对。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在中国书坛崛起的一个流派。它的特征是反正统,变乱笔法,告别经典。有偏激者,甚至称经典是废纸,王羲之已过时。观念不同,必然导致笔法的不同和艺术境界的差异。正统书风追求永恒的经典、优雅,“民间俗书派”则竞奇尚拙、偏执丑怪。结果是给中国书坛在某些局部,引来了前所未有的人人竞丑之风。有些展览,人人竞为丑、傻、狂、怪……着实给书坛带来了不小震动。细考起来,“流行书风”应该说是九十年代中国书坛的一次“平民化”运动。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以平民为美的标准(改变审美标准),二是让平民进入书坛(改变精英独霸的历史传统)。它的历史动力是于正统外“别开户牖”、“自立门户”。它的美学思想渊源远追其源是中国文人早已有之的“异态美”思想——如苏轼:“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2];刘熙载:“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3]现实的直接诱因则是展览的“展厅效应”[4]。社会心理根源则是艺术投入的商业思考:走捷径,小投入,快回报,早成名。因为正统的道路要求全面深入学习经典,投资周期长、投入大、效益低、回报慢——且要超越历代经典,可谓关山万重,谈何容易!而从笔法稚拙的民间俗书中找一点异态形式,以此发挥开去,巧加组合,就可能很快能形成个性较强的风貌,赢得书坛的关注。著名书家苏士澍先生在2003年在接受《书法》杂志的采访时曾说它是“以标榜个性掩饰传统功力的不足”、“反映了部分书家急功近利、浮躁的心理”,我觉得是中肯的。当然,这种创作思维及其形式成果,对丰富中国当代书法不能说没有贡献。无论如何,它促进了中国当代书法的多样化,在正统之外,也确实是别开“奇”、“丑”一境。但鄙意认为有两点应注意:第一,“民间俗书派”取法对象是残砖烂瓦、书记账簿,多出村夫野妇、引车卖浆者流之手,属历史上的低教育阶层;即便“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借鉴这些原始粗朴的生活“废料”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倡去芜存菁,取其精华,要“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而不能原封不动不加过滤地接受,把自己降到村夫野妇水平。第二,村夫野妇作书多率意而运,无谈笔法、字法,更难有人文境界。在教育领域,恐怕不宜推广。如果强称这就是书法艺术的未来,大家都要跟着走,不跟着走就是废纸,那就恐怕不妥当了。
3、现代派:前两种都是传统派,是中国书法文化体系内的学术裂变。现代派则是在外来文化碰撞下发生的。其涵盖面也很广,大都有比较明显的“西方文化中心”倾向。他们中间也有很多分支,与传统书法的血缘关系远近各有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对西方文化的“仰望”心态,希望中国书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文化接轨,进入建立在西方思想价值观念基础上的现代艺术体系。从融合中西,推进书法艺术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这一点上说,动机应予肯定。
中国的“现代派”书法的产生,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日本“前卫书法”。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始,日本书家就有“书法美术化”的动议。如被称为日本现代书法鼻祖的比田井天来(1872—1939)1921年就提出“实用书”和“艺术书”分开的主张。1933年,他和学生创建“书道艺术社”,推广自己的艺术理念。“二战”结束后,书法美术化的运动——“前卫书法”或“墨象派书法”在日本快速发展,八十年代后也回流影响了中国。这是第一方面原因。第二方面原因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现代艺术、哲学、美学大量译著在中国出版。中国艺术不再是游离于世界艺术潮流之外的孤岛。书法也是如此。在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影响下,在中国艺术内部,也出现了“嫁接”西方现代艺术对书法进行“改造”的思想。内外力量呼应互动,催生了中国艺术界新的“书法”流派——其中有的可能还可称书法,有的我以为已远离书法了。在众多的艺术流派中,笔者根据其艺术特征,归为三类:一是“书法主义”,二是“学院派”,三是非纸上“书法”。“书法主义”和“学院派”都以引进现代美术观念,突破传统手法,拓展书法表现空间为特征,但本质上它们又很不同。
“书法主义”以日本“少字派”、“墨象派”为母本,加入了多种不同艺术家个人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理解,试图在笔墨和空间形式内加以诠释、表现,其外在形象接近现代抽象画。他们的口号是“和汉字脱籍”,形式上经常是把汉字大卸八块,“画面”的汉字经常支离破碎,难以辨识。在外观上,这是一个张狂的叛逆者,和传统的书法已经距离很大,似乎已完全另类。但是我认为,“书法主义”与传统书法是“貌离神合”,形式上距离很大,精神实质还是血脉相连。一字书也好、二字书也好,三字、四字也好,“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汉字顺序书写”原则并没有改变,只是突出、放大了一些。少字作品在中国传统书法中并不少见。不过古代的少字作品,笔法、构图传统的,汉字语义可以直接阅读而知;“少字派”、“墨象派”、“书法主义”则通过变形、肢解等手法,消解了书写汉字的直接可读性,字形变得扑朔迷离。所以形式上好像离经叛道走得很远。实际上,我觉得它们张牙舞爪、疯狂咆哮、腾挪跳跃,最后还是不离故处。它只不过是把传统书法的某一个“点”(用笔、构字、墨法等)作了局部的超巨型放大。我们试把古代书家的大草作品在电脑里作局部放大,可以发现有很多类似的构图和效果(当然问题决不会是那么简单),说明它们和传统经典,仍然是血脉相连;至于笔墨间流露的黑色馨香和黑白间美的浅吟低唱,更是展示了它和母体书法的同宗关系。所以我以为,“书法主义”和“流行书风”一样,还是书法内部的学术之变
“学院派”同样产生于“书法创新”的大潮中,它的思路与“书法主义”大不一样。“书法主义”是“貌离神合”,“学院派”是“貌合神离”。“学院派”作品,是借鉴了美术作品创作的方法。它强调工艺制作(“技术品位”)、作品的形式感(“形式基点”)和独立主题(“主题要求”)。这些,与我们传统书法所夙求者,已非出一格。它的作品形式,大量的是不同时空书写的汉字群组的集拼;或一个画面内,或多个画面组合,加上空间、色彩运用。局部看,很书法;但四五件旨趣不同的书法“部件”拼合在一起,实际上,原有的书法“部件”在新“画面”拼合的“二次创造”中,其作为独立的书法作品的艺术品格已被废黜、消解;拼合后的部件,就像电影的“蒙太奇”,在拼合中已自然转换身份,去组构一种新的画面“诉说结构”。从拼贴、组合这一点看,“学院派”是借用了西方现代艺术中“波普”手法;从作品展示的内蕴看,作为组件的“书法”及其附有的笔墨神韵,因为组合中“身份”的改变,已不再拥有作品欣赏主体地位;艺术家创作的意图,也不再是展示拼贴组件中的汉字书法的笔墨神韵,而是从组件的“拼帖组合”中寻找当代人对中国书法艺术、推而广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思索、表述。因而,书法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些“拼贴艺术家”“文化诉说”的奴婢。既然汉字书写的单一时空顺序已被多重时空交迭的“拼帖”所取代;书法审美的诸多元素:汉字语意美、线条力量美、造型姿态美等,在“学院派”的作品中都已退居其次,成为这些“拼贴艺术家”的“文化冥想”与“诉说”的道具,那么如果我们不改变书法的定义、不扩大书法艺术的外延的话,我们恐怕很难接受“学院派书法”是一种书法的创新,或者说是书法艺术的“现代化”尝试。其实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大背景来审视“学院派书法”,我觉得现在冠以“学院派书法”的这种艺术,放置于“当实验艺术”更合适,它是一种糅合书法与美术、处于书法和美术边界的实验艺术。前无古人,当然是一种创新。它试图以书法和相关视觉素材为“文化语符”,进行某种有意图的拼贴,借以表达某种文化反思。这无论是对传统书法还是传统美术,都是极大的突破。只有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流有了相当积累、中国艺术家兼具中西学术资养的前提下,才可能培育出这样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否成功,只能由历史老人提供答案,我们现在说一切都过早。至于我们是否把它归入书法,我相信这完全不影响它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地位。
非纸上“书法”,即以书法为一个文化要素或形式支撑点,而进行的其他相关艺术活动——如“行为”书法、“装置”书法等等。我认为这些也都是“非书法”,它们的合理身份标签应该是“中国当代实验艺术”,属于中国当代美术“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凡仅仅利用书法作“艺术诉说”道具,而不是把书法当作艺术主体,以其法定身份作全面艺术内涵展示者,都不能列入书法。充其量,这些只能说是一种与汉字书写有关的艺术。
三、结语:书法文化建构
厘清概念,是为了避免混乱,也为了明确方向。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坚守民族艺术的纯粹性,对我们书法艺术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认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审美语言体系,以及这个话语体系所体现出来的东方艺术智慧,远远还没有被世界了解、认知。立足于汉字书写而形成并构成东方造型艺术语言基础的中国书法艺术,我想应该像欧洲古希腊的雕塑、中世纪的建筑一样,也是人类理性、智慧在某一方面投入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杰出成果,世界艺术史应该有它应有的篇幅。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一点,远远未被世界所了解。因此我们要好好加强研究和阐述、宣传、传播,让更多的世界目光关注中国文化、关注中国书法,推动我们的中国书法的艺术独创性和普遍美学价值,获得更多世界认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学院派”也好,“非书法”也好,它们不是我们所认同的书法,但我们也不应视其为“异端”甚至“洪水猛兽,绝对不能!它们应该是我们书法艺术的盟友。因为他们取资于书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推广了书法。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在众多新的大众审美、娱乐形式的竞争中,传统艺术都是弱势群体。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界外关注”、“界外介入”和“界外征用”,以便使书法艺术获得更多的社会应用、更多的外围支持,藉此而获得更坚实的社会基础。把这些友军都接纳进来,一方面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加强传统输出,使优秀的民族艺术精神向更广阔的领域辐射、传播。所以想到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与文化建构,我希望“文化建构”的范围能够大一些,把所有跟书法相关的事物,都涵盖进来。既然是“书法文化”——书法之“文”(由纹彩而引申为美的形式)之“化”(改变、影响、征服),那么所有那些对书法心存仰慕、在艺术上积极开展“二次”开发和“再生”“再植”“再造”的艺术运动和艺术家,理应都在此之列。
注:
[1]张怀瓘《文字论》。
[2]苏轼《和子由论书》: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橢。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
[3]刘熙在《艺概:“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丑字中丘壑未尽言”。
[4]在展厅中形式怪诞者更具视觉冲击力,易于引起注意。